摘要:阿摩司·奥兹是一位有着女性想象自觉的作家,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具有恋父、背叛传统、单恋欧洲倾向的女性群体, 该群体印证了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恋父行为体现了女性被支配、被操纵、主体性被剥夺的事实;女性尝试以叛逆行为实现突围, 突围的力量源于父权的生产性与女性的边缘化益处;身处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文化夹缝中的犹太女性产生了比男性更为强烈和持久的身份困惑与信仰危机。这些女性因承载着奥兹的个人思考而成为其对话尝试与主体间性探索的载体, 成为其对自身男性、犹太人、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进行确认的镜像。
关键词:阿摩司·奥兹; 女性镜像; 权力; 主体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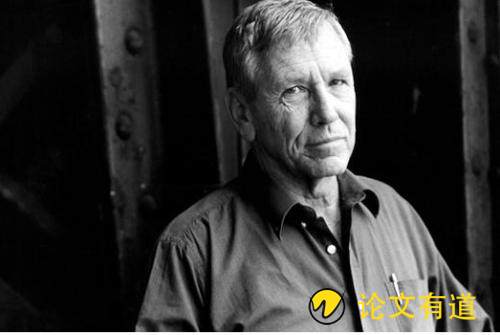
阿摩司·奥兹是一位有着女性想象自觉的男作家, 他擅长用小说这一大容量载体将其丰富的女性想象充分地表现出来。奥兹小说中的女性镜像承载着作家对于犹太社会宗教、文化、性别等各场域复杂权力运作的思考, 体现了作家对两性主体间性的积极探索。
一、女性想象的自觉
男作家自觉的女性想象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对于“女性书写”,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解释迥异于英语“feminine writing”的作者性别所指, 如西克苏等认为“女性书写” (écriture feminine) 指涉的是作品属性, “署上女性的名字并不一定保证这部作品就是具有女性特征的……一部署名男性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排除女性特征”[1].理论上, 作品的性别属性与作者的性别属性可能产生错位, 男作家可以自觉进行女性想象甚至女性书写。因话语障碍和先验心理结构差异的存在, 相对于女性书写, 男作家自觉的女性想象更为可行。爱情与婚姻是女性生活的中心图景, 对女性婚恋描写的自觉常体现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与生存体验关注的自觉。
实践层面上, 众多男艺术家都曾对女性进行过自觉想象。中国文化界20世纪20年代倡导“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 男作家们通过写作自觉探讨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周作人提倡“女子本位”性观念;张资平出于对男性的“性别无意识”的警醒, 描写了馨儿、苔莉、静媛等具有新性道德意识的女性形象;茅盾在其小说中反省男性的性别无意识并塑造了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一系列觉醒的新女性。在西方, 西班牙男导演阿尔莫多瓦因在电影中生动展现了女性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而被赋予“女性导演”的头衔[2].
特殊的经验形成作家特殊的前理解结构并影响作家的创作倾向。奥兹有着明显的恋母情结[3], 但12岁时其母自杀。本着“你身在哪里, 哪里就是世界中心”[4]的原则, 奥兹根据自身经验进行创作, 通过自觉描写20世纪巴勒斯坦犹太女性的生存困境来疗治心灵之痛, 找寻母亲的自杀原因。
继承与创新的创作语境也激发了奥兹女性想象的自觉。19世纪以来的希伯来小说有两大走向:门德勒开创的社会经济、政治表现走向与弗里希曼、别尔季切夫斯基首创的心灵世界展现走向。阿格农另立一宗, 使两者达到完美平衡[5]14.奥兹本人深受阿格农与别尔季切夫斯基的影响。同时, 奥兹是新浪潮作家的一员, 新浪潮作家的小说往往与社会现实 (通常是边缘现实) 保持一致[5]244, “保持个人经历与他和民族无法摆脱的联系之间的微妙而又适度的平衡”[6]11.所以奥兹比较富于自我意识, 其小说摈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通用情节, 不再描写先辈“帕尔马赫”一代作家笔下的那些带有意识形态先驱色彩的复国主义理想人物, 而倾向于通过描述处于边缘地位的现代犹太女性的生存感受来表达自己对犹太人个体生命体验与群体生存状况的思考。
二、阿摩司·奥兹的女性想象
奥兹将其自觉的女性想象诉诸小说文本, 塑造了恋父者、叛逆的“家庭中的天使”、欧洲的单恋者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 部分女性甚至兼具其中的两种以上特征。恋父情结、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对欧洲的单恋深刻影响了这些女性的婚姻与爱情。
(一) 恋父者
奥兹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恋父倾向的女性形象。一部分女性在维持与父母的情感联系时严重倾向父亲一极, 对母亲持排斥态度或有明显的负面情感, 如《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范尼娅姐妹热爱父亲但视母亲为性格乖戾的暴君;《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声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当中, 我最爱的是先父”[7]2, “母亲在我心目中是那么微不足道。她是父亲的妻子。仅此而已”[7]228, 她甚至憎恨母亲对父亲的偶尔顶撞;《莫称之为夜晚》中诺娅与父亲相依为命并耗费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悉心照料年迈的父亲;《了解女人》中因对父爱饥渴, 妮塔四岁就开始用癫痫病绑架父亲, 她嫉妒并攻击母亲、父亲的情人甚至想与父亲建立亲密友谊的男人。另一部分女性在恋爱与择偶上表现出明显的恋父倾向, 如《何去何从》中诺佳对父辈的埃兹拉产生了暧昧的感情;汉娜遵从父亲告诫婚前远离肉体诱惑, 因父亲终生崇拜学者而压抑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嫁给学者米海尔;诺亚的恋爱对象分别为年长的同事、老教授及年长自己15岁的西奥。
(二) 叛逆的“家庭中的天使”
在犹太传统中, 女性应是“家庭中的天使” (the Angel in the House) , 在尽心尽责履行家庭内部责任和义务的同时, 要具备一系列美德。拉比们对夏娃所表征的女性规则进行了阐释:神用来造女人的部分是人体上最为谦卑的部位, 所以夏娃代表谦逊品质。在该思想之上, 拉比们敷衍出犹太女性的行为规则:女性被造的最高目标是“为人母”;女人应该是善于理解的;女人必须处于婚姻状态中, 并且她们对婚姻是极其重要的;女性要谦逊、仁爱、忠诚、驯服、皈依公义, 而在婚姻与为人母的过程中完成自身义务的路得为一切犹太女性的典范[8].
但奥兹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女性, 叛逆了的“家庭中的天使”---这些女性拒绝遵守传统犹太社会为她们制订的行为规范,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些女性的第一种行为倾向是背叛忠诚原则。《何去何从》中的伊娃与堂兄弟私奔, 其女儿诺佳婚前被强暴, 16岁生私生子;《鬼使山庄》中的鲁思抛夫弃子, 与好色成性的英国将军私奔;《黑匣子》中, 身处第一段婚姻时伊兰娜的私生活一度成为全城丑闻, 第二次婚姻中她又与前夫阿里克斯纠缠不休;《莫称之为夜晚》中诺娅的母亲与情人私奔;《空心石》中的马蒂雅一度放荡堕落;《了解女人》中的伊芙瑞娅与单恋自己的男邻居一起触电身亡。
第二种行为倾向是背弃谦逊与仁爱原则。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中的坦尼娅是疲惫、刁钻、爱抱怨、富有攻击性的庸俗妇人;《志未酬, 身先死》中的扎什卡暴戾、自私、狭隘;《怪火》中莉莉两次婚姻共维持七个月, 她诋毁女儿的爱情并勾引女儿的未婚夫;《空心石》中的马蒂雅虐待女儿迪查, 步入老年后变得尖刻、自私, 迪查虐猫并叛逆。
第三种倾向是背离智慧原则。《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沉溺于白日梦、自虐并最终自杀;《沙海无澜》中的丽蒙娜以睡美人般麻木、迟钝的态度与丈夫相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范尼娅患严重抑郁症之后自杀身亡;《游牧人与蝰蛇》中葛优拉因不受异性青睐而倍感孤独, 与贝都因人的相互吸引无疾而终后, 她试图以臆想中的性袭击煽动基部兹针对贝都因人的复仇行动;《空心石》中马蒂雅将女儿迪查当作假想中的情敌;《在这邪恶的土地上》皮特达恋慕父亲并视自己的燔祭仪式为两人的婚礼;《风之道》中23岁的莱雅·格林斯潘陷入情网, 却只成为56岁的工人运动领袖施姆顺·欣鲍姆传宗接代的工具;《特拉普派隐修院》中的布鲁瑞只是英雄以彻激烈战斗之后的肉体慰藉并被其粗暴对待, 但她依然疯狂崇拜并爱慕以彻。
(三) 欧洲的单恋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排犹浪潮而非复国主义理想迫使大批犹太女性移居巴勒斯坦, 但她们无法适应巴勒斯坦的生活, 也无法在当地犹太社会获得归属感。如汉娜的内心独白反复强调:“我不知道有谁会把耶路撒冷当成家园……我写下‘我生在耶路撒冷'.我不能写’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这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城市。”[7]91“遥远的我再也不爱耶路撒冷了。她希望我坏。我盼她不好。”[7]229范尼娅一旦回忆往事, 内心就充满了苦涩与绝望, 其好朋友声称“生活在此地就像噩梦”[9]213.她们甚至对栖身之地巴勒斯坦表示仇视或者鄙夷。鲁思不到一年就厌烦了这个国家和它的语言;《我的米海尔》中的杰妮娅以欧洲人自居, 认为当地医院堪比最糟糕的亚洲医院;尽管移民前后的物质条件差别并不大,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施罗密特第一眼看到耶路撒冷便做出“黎凡特到处是细菌”的终极裁决并最终死于抵制心理产生的洁癖;《何去何从》中, 伊娃认为巴勒斯坦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国家”, 称在巴勒斯坦暴雨之夜“希望去死”[10].
这些女性执着地单恋着欧洲, 其“应许之地”是欧洲而非巴勒斯坦。她们保持着欧洲式的衣着、时尚和行为举止, 谙熟欧洲的多种语言与艺术, 笃信欧洲价值观。对于她们而言, “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9]2, 甚至真正的生活“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欧洲”[9]17.
对“应许之地”的向往使她们无法面对巴勒斯坦包括失业、物资奇缺及安全匮乏诸问题在内的艰苦生活。最终她们以各种消极方式奔赴她们的“应许之地”:伊娃抛夫弃子与堂兄弟私奔到了慕尼黑;失去诗歌、舞会、束腰长裙和真丝围巾的鲁思常年蜗居于石砌小屋中, 被大屠杀幸存者噩梦中的惊叫刺激着神经, 她变得歇斯底里, 甚至对着年幼的儿子发泄自己的绝望[11], 后委身于好色猥琐的英国将军以逃离巴勒斯坦;汉娜身居丈夫的客厅却思考“我为什么被流放至此?”[7]141并最终自杀;米娜离开丈夫伊曼纽尔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故乡;范尼娅患抑郁症并以自杀逃避让其绝望的匮乏和无聊。
三、女性想象中的权力问题
用拉康、伊蕊格莱、福柯与布迪厄等人的观点来看, 奥兹小说中犹太女性的恋父、反抗传统、单恋欧洲倾向源于其所在的性别、宗教、文化、政治诸场域复杂的权力运作。
(一) 恋父:被控制、被操纵与主体性的被剥夺
拉康认为, “父亲”的所指对象是象征性秩序, “父亲的形象作为纯粹的能指是一切约束性规则的来源和依据, 对主体来说, 是既定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的一种标志”[12].该象征性秩序的约束性实际上体现为权力, “能使别人服从掌权者意志的力量, 即个人、集团或国家贯彻自己的意志或政策以及控制、操纵或影响他人行为 (而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的力量”[13], 具有主体的意志性、不平等性与支配的强制性三个明显特征。相应的, 女性的恋父心理与行为体现了父亲的意志及其权力的强制性特征, 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性的匮乏。
同样, 在女性主义理论视阈下, 父亲作为父权的执行者而出现, 恋父情结与恋父行为体现了女性的被支配、被操纵、主体性被剥夺的现实。如伊蕊格莱 (Luce Irigaray) 对父权的运作过程做了深入的研究:男人先建构自己的形象并树立父权体制, 再依照自我形象将女人作为自己的镜像来关照, 长久生活于该体制中的女性丧失主体性, 最终成为父权制的镜像。而“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 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 是一种性的欲望, 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 在顺从和崇拜中, 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14].奥兹小说中的父亲对女性的个体情感具有高度的规定性, 父亲这一群体甚至使她们排斥包括母亲在内的父亲的伴侣, 在择偶上遵循父亲制订的规范, 或者选择父辈男性作为伴侣。这些女性根本不曾拥有独立的个体情感和生成独立个人情感的空间与能力。
(二) 叛逆:觉醒后的突围
1. 女性的传统角色分工
在犹太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中, 犹太女性不应致力于事业上的成功, 而应以家务为重, 追求事业的女性会被批评, “你瞧那个自私的女人, 她出席各种会议, 而她可怜的孩子在街上长大, 付出着代价”[9]182.所以, 奥兹小说中的范尼娅、汉娜、鲁思、伊兰娜、伊芙瑞娅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家庭主妇。
犹太传统文化还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在犹太人看来, 在公共场合, “犹太妇女应该尽量少抛头露面, 尽量少说话”[15], “一个犹太家庭主妇, 作为’家中的天使‘”, “她的任务是保证食物充足、房间整洁, 而不必和客人谈话”[16].奥兹描写了女性的这一处境, 在其小说中女性“总是在厨房、储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 “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9]56、一直保持沉默的“非凡的听众”, 她们不得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范妮亚在丈夫那里只能倾听而不能接话茬, 阿格农当众嘲讽偶尔发出尖利声音的夫人, 甚至连孩子都会为母亲打断男性的谈话而苦恼---当时赞美女子要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 却从来不会赞美一个女子有高明的见解, 因为介入谈话的女性是不受欢迎的。
女性主义学者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做出过生动的描述:“女性一直是男人的奢侈品, 是画家的模特, 诗人的缪斯, 是精神的慰藉, 是护士、厨师, 替别人生儿育女, 是他们的文秘和助手。”[17]“女性什么都是, 唯独不是她自己, 长久地陷入毫无创造性的琐碎家务中……周而复始,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在机械与重复中, 主妇在原地耗尽自己的一生。”[18]奥兹小说中女性对其所处地位, 对“家庭中的天使”这一角色有着清醒的意识, 如伊兰娜对丈夫满腹牢骚, “见鬼, 他干嘛就觉得只是在家里待一天就配得一枚英雄勋章而我就该在这里厮守一辈子?……我不是他的女仆”[19].范妮亚重度抑郁、濒临自杀时无休无眠地阅读描写犹太女性生存感受的《锁柄集》以寻找精神寄托。对自身地位的清醒认识使这些女性厌倦“家庭中的天使”这一角色分工, 在绝望中, 她们尝试以自己的叛逆行为进行突围。
2. 突围的力量:源于权力的生产性与边缘化益处
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犹太教育观念的最核心部分, 对犹太人犹太性的延续、犹太民族的复兴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正统犹太教主张父权, 相应地, 传统的犹太文化和犹太教育模式体现出鲜明的父权制特征, 如学龄期的犹太孩子就已经被灌输了“男尊女卑”的观念[20].在20世纪之前的犹太教育模式中, “男人, 身份较高, 承担着保证犹太教的精神生存和宗教生存的责任;女人, 身份较低, 掌管着世俗事物。由于这一社会性别角色的划分, 必须得把女人排斥在研习《托拉》的领域之外……女人担当着养家糊口的角色, 这就需要她们和基督教环境接触, 向社会倾斜, 允许她们学习外语, 并获得世俗教育”[21].
关于权力的运作, 福柯在《认知意志》中, 以忏悔 (confess) 的演变过程论证了权力对性话语的煽动, 质疑“性压抑说”, 从而说明权力的运作不是简单的禁止, 其生产、肯定、积极性质比压制、否定、消极性质更为根本, 而且前者正是依赖后者得以运行。传统犹太文化尤其是传统犹太宗教教育对女性的否定、压抑与排斥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意义与生产功能:在哈斯卡拉运动以前的犹太神权社会发展阶段, 犹太女性与宗教这一主流话语疏离, 开始接受世俗教育;哈斯卡拉运动之后, 犹太女性与男性相比, 更接近欧洲思想文化。于是, 与“隔都”或“精神隔都”中固守传统的男性群体相比, 传统犹太文化和教育体制赋予的边缘化地位使女性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使她们有机会走向非犹太文化尤其是现代欧洲文化。
中世纪以来欧洲女性的地位持续上升。十字军东征期间贵族女性便获得了家庭财产的拥有权和管理权并涉足公共领域[22];拜占庭的圣母崇拜被带回到欧洲, “使得女性不再是等同于夏娃 (堕落女性) 的单一形象”, “骑士爱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 带来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骑士传统和绅士风度[23].之后, 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使平权思想深入人心;工业革命之后女性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以后, 女性争取自身平等政治、经济权利与文化地位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完备的世俗化教育使犹太女性与欧洲女性的思想发展趋于同步。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柏林的沙龙代表了沙龙发展史上的高峰, 而这些沙龙的创办者主要是犹太女性。这些女性因在沙龙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和丰富的文化修养而“引人瞩目地跻身于当时社会文化领域的中心, 被视为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24]208.
“沙龙犹太女性所受的严格世俗教育恰恰弥补了她们传统宗教教育的缺乏, 这不仅使她们一旦面对外来文化比男同胞更容易疏离犹太教, 而且也很难承担起传统犹太妇女的角色, 她们中的不少人就没有生儿育女。”[24]212同样, 奥兹笔下这些叛逆传统的女性大都有着良好的世俗教育背景。伊娃音乐天分非常高;范尼娅曾在布拉格大学与希伯来大学跟随名师攻读历史和哲学, 并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鲁思、汉娜、诺娅曾在大学攻读文学;伊芙瑞娅曾攻读硕士学位;伊兰娜是着名周报的编辑;米娜和《费玛》中的约珥甚至分别是杰出的医生兼学者、研究喷气式汽车的科学家。良好的世俗教育使这些现代犹太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去传统倾向。
(三) 对欧洲的无望单恋:文化博弈中的被动选择
布迪厄认为, 在人类文化体系的各类场域中, 在惯习的辅助作用下, 由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等类型资本组成的符号系统承担了社会区隔功能。奥兹小说中犹太女性对欧洲的单恋, 正是社会符号系统暴力统治的结果---欧洲社会拒绝了这些认同欧洲文化但兼具犹太身份的女性, 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则强力抑制她们的欧洲特征、野蛮入侵其私人生活领域并将其边缘化---在文化场域各种力量的博弈中, 身处巴勒斯坦但四处碰壁的犹太女性受制于惯习的约束, 最终将精神归宿置于欧洲这一来处。
1. 大流散语境中的文化消解
第二圣殿被毁以及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 犹太民族的主体开始了近两千年的大流散历史, 流散在五大洲的犹太人散存于异质文化中, 散存结构成为犹太文化的整体结构特征[25].在该结构中, 处于弱势地位的犹太人以适应和吸收的方式与客居地文化进行接触, 犹太人或迫于强权或主动皈依而走向同化, 强制性同化和自然性同化成为犹太文化和客居地文化的重要联系方式。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推行的强制性改宗运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的排犹运动等, “种种迫害就其文化本质而言, 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以不同方式对犹太人进行的诸种强制性文化同化与’文化消解‘”[26].
自然性同化往往发生在客居地的文化宽容度较高并表现出强大的诱惑力时, 如历史上“以色列十族”的消失。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西方民主化等也促进了传统种族、民族与宗教偏见的消退, 犹太人融入西方世界成为可能。犹太人的启蒙运动哈斯卡拉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哈斯卡拉运动的目标在总体上是以鼓励犹太人通过世俗教育, 广泛接触和吸收欧洲文化的方式, 在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中悄悄地引起一场变革, 最终塑造出能在思想上摆脱传统束缚, 在思想和经济上适应欧洲主流社会的一代新型’现代‘犹太人。”[27]279该运动大大加快了犹太人的欧洲化进程。犹太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在不断发生改变, 以至于“到了19世纪, 犹太人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东方人了, 而是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成员”[27]52-53.
而正如前文所述, 犹太女性因接受了更多的世俗教育, 对欧洲文化的认可度更高, 如门德尔松的长女多萝西娅 (原名布伦德尔Brendel) 和在德意志地区创办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的亨丽埃特就已经受浪漫主义宗教观的影响而选择改宗。但是即便是主动走向文化同化、主动皈依欧洲文化的犹太女性, 在付出放弃自身传统的高昂代价后, 仍然不能被欧洲人真正接纳。雅各·卡茨就曾指出, 虽然具备德国中产阶级的部分特征, 犹太人整体最多作为亚群体存在于德国社会[28].奥兹笔下对欧洲文化有着更多认同但因欧洲日盛的排犹主义而被迫移民巴勒斯坦的女性内心有更为强烈和持久的信仰危机和身份困惑。
福柯认为, “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的, 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 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29].所以, 即便是包括哈斯卡拉运动本身在内的自然性同化, 背后都隐藏着强制性的文化规范和权力运作:强势文化对异己的弱势文化的排斥与消解。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弗朗兹·法侬曾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了文化同化给被殖民者带来的极度扭曲心理:嫉妒、羡慕使被殖民者通过模仿殖民者来实现做主人的幻想, 在这个过程中被殖民者创造性的消失并成为殖民者的衍生物。遵从同一逻辑, 犹太女性被同化、认同欧洲文化、单恋欧洲的过程, 是其作为犹太人创造性的消失、演变为欧洲文化衍生者的过程, 其单恋是强势的欧洲文化与弱势的犹太文化两种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
2. 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语暴力与阶层区隔
犹太人文化同化的结果之一是其文化身份的再造。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因兼具客居地的文化特征而拥了多重文化身份, 如希夫就曾声称:“我可以一分为三:我是个美国人, 我是个德国人, 我是个犹太人。”[30]犹太女性因接受了更多世俗教育, 文化身份的多重性特征更为鲜明。但具备多重文化身份的犹太女性在被迫移民巴勒斯坦后要面对诸多认同问题, 首要的便是对复国主义主流话语的融入障碍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既指犹太民族“还乡复国的思潮, 也指犹太人以还乡复国为宗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其目标是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 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权民族的国家, 复兴整个犹太民族”[27]286.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工党建国三原则之一在以色列建国中起了关键作用。建国前劳工党在诸多政党的竞争角力中胜出, 建国后其统治延续到1977年, 犹太复国主义自然成为以色列建国前后几十年间的主流价值观。
犹太复国主义话语符号系统对异己话语实行暴力统治。“以色列在建国之初, 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 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31]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倡导单一的国家认同, 强调集体主义、拓荒精神和积极进取意识, 其他类型的文化与情感诉求被抑制, 甚至连大屠杀幸存者都被鄙视和排斥。奥兹笔下的犹太女性多为流散于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在传承祖辈文化的过程中, 欧洲文化已经融入她们的血液甚至成为她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同时, 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她们已经历史地形成自己丰富独特的个人特征。但她们不被主流话语理解、同情和接纳, 复国主义话语甚至要求她们抑制进而生硬地阉割掉这些根深蒂固的个体与亚群体特征, 其中包括习俗、语言、思维方式、习惯、爱好、审美等。奥兹对此做了戏谑的描写, 如“母亲讲四五种语言, 能看懂七八种。……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 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 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9]2.
同时, 与神权社会阶段犹太女性与宗教疏离的状况相似, 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阶段, 犹太女性与复国主义这一主流话语疏离, 但复国主义话语对女性私人生活领域进行了长驱直入的入侵。奥兹小说描写了这种现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 人们“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 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 干巴巴, 甚至诚惶诚恐”[9]11;“犹太复国主义激情使父亲尤其为之沉醉”[9]277, 他甚至认为家庭聚餐时“最紧迫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肯定是在朱迪亚沙漠里发现的死海古卷”[9]511, 并将该话题从上汤持续到上主食, 对此范尼娅无法忍受;《了解女人》中优秀的摩萨德成员约珥几乎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于间谍事业, 他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使女儿恋父并憎恨母亲, 妻子伊芙瑞亚自杀;《费玛》中费玛因热衷于政治而对妻子孕育的孩子毫无兴趣, 甚至为与朋友讨论政治问题让妻子约珥独自去堕胎;《黑匣子》中伊兰娜的东方犹太人丈夫狂热地投身于“新锡安主义”, 夫妻两人渐行渐远。
复国主义主流话语还具有阶层区隔作用:拓荒者因在以色列国家建设中所起的奠基作用而被视为“大地之盐”, 站在以色列声望之梯的最高端;拓荒者之下是附属阶层, 最底层的是其他人[9]13.这种区隔具有强大力量, 人们连在思考“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 送哪种花”这样的问题时, 都要反思“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在加利利, 拓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9]19-20.奥兹甚至通过投身基部兹来斩断自身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特征, 斩断自己与大流散的联系, 试图把自己改造为拓荒者一员。奥兹笔下的阿什肯纳兹中产阶级女性接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 与拓荒者、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们相去甚远。在性别与社会阶层的区隔作用下, 她们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
奥兹笔下的身处巴勒斯坦犹太社会的中产阶级女性对其边缘地位, 对复国主义的话语暴力与社会阶层区隔有着深切的感受与清醒的意识, 她们的压抑感、厌倦感与日俱增, 遂将“应许之地”寄托于来处---欧洲。
四、主体间性探索
奥兹对女性所处政治、宗教、文化、性别等场域中的权力运作的披露, 体现了他对男女两性主体间性的自觉倡导。
哈贝马斯认为, 个体性主体的膨胀制造了启蒙和现代性的困境, 解决方式是建立交往理性, 相应地, 主体性应该被复数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取代。主体间对话关系的建立是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建立的基础。奥兹是一位倡导对话的作家。奥兹认为“好的小说……不是黑白分明的, 也没有对与错……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故事, 而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与战争”[32].对此学者郑丽运用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的对话哲学 (Philosophy of Dialogue) 分析奥兹小说, 认为奥兹小说因探讨了对话这一冲突和分歧的解决方法而具备了深邃的哲学思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33].
奥兹还屡次通过小说人物呼吁男性在两性主体间性构建过程中做出努力。首先, 男性要自觉将女性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群体。深受女性欢迎的亚历山大声称“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是作为人的女人”, “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只是满怀敬意地看着她”[9]121, 而范尼娅自杀前告诫年幼的儿子, “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宝贵珍奇”[9]512.其次, 要尊重、探索并认可女性群体的差异性。93岁的亚历山大坦言, “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 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我依然在探讨”[9]121;费玛年迈的父亲直言“从某些方面来说……女人和我们男人没什么两样;但从其他方面来说, 男人和女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至于哪些方面一样, 哪些方面又不一样---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34].奥兹擅长设身处地, 立足于人物所处情境, 站在写作对象的立场进行写作。奥兹的这一自觉意识也投射在作品中, 其部分男性角色开始觉醒, 开始学习设身处地, 立足于女性所处的情境与立场去处理两性关系问题。如小说《沙海无澜》中的约拿单经历了“躁动---出走---回归”式的人生探索后, 逐渐成熟并开始思索自己与妻子间的关系问题, 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之前在两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非常深入地思考了女性的生存状况问题, 但身为男作家的奥兹并不能真正开启女性的语言系统。“’镜像‘常常是在视角定格之后, 印证着线索、含蕴着意义的外在化了的文学形象”[35], 奥兹小说中的女性镜像印证了作家的理性思考。拉康用“镜像”这一概念来阐释主体的形成过程:儿童通过镜中形象确认自身并获得整体性, 该“镜像阶段”的完成依赖于想象;在主体趋向于整体性和自主性的这一努力中, 自我的对应物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以奥兹的对话逻辑和“镜像”原理来推论, 奥兹小说中身处第二性与认同困境中的女性在担负规约文本意义这一责任的同时, 还因承载着作家的个人思考而成为其对话尝试与主体间性探索的载体, 成为其对自身男性、犹太人、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进行确认的“镜像”.
参考文献
[1] Hélè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J].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81 (1) :41-55.
[2] 李简瑷。阿尔莫多瓦的女性镜像与后女性主义[J].电影文学, 2006 (14) :20-23.
[3] 李沁叶。论阿莫司·奥兹小说对女性脆弱物质承受能力描写背后的俄狄浦斯情结[J].语文学刊, 2009 (10) :87-88.
[4] 钟志清。阿摩司·奥兹以写作寻求心灵宁静[N].中华读书报, 2007-08-29 (5) .
[5] 格尔绍恩·谢克德。现代希伯来小说史[M].钟志清,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6] 亚伯拉罕·B·约书亚。三天和一个孩子[M].陈贻绎,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7] 阿摩司·奥兹。我的米海尔[M].钟志清,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8] 陈艳艳。《希伯来圣经》和拉比文献中妇女观的比较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15.
[9]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M].钟志清,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10] 阿摩司·奥兹。何去何从[M].姚永彩,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62-63.
[11] 阿摩司·奥兹。鬼使山庄[M].陈腾华,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22.
[12] 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18.
[13] 孙国华。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342.
[1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32.
[15] Swidler, Leonard. Women in Judaism:The Status of Women in Formative Judaism[M]. Metuchen, NJ:Scarecrow Press, 1976:123.
[16] 肖飚。从互文性视角解读辛西娅·欧芝克小说中的女性表征[J].外语教学, 2014 (3) :77-79.
[17]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122-142.
[18] 赵思运。呻吟中的突围--女性诗歌对男权镜像的解构与颠覆[J].文艺争鸣, 2001 (1) :54-61.
[19] 阿摩司·奥兹。黑匣子[M].钟志清,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191.
[20] Susan WEIDMAN. Jewish and Female:Choices and Changes in Our Lives Today[M].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4:284.
[21] 伊里丝·帕鲁士。 19世纪东欧犹太社区中的女读者[J].钟志清, 译。中国图书评论, 2009 (4) :29-32.
[22] 徐善伟。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J].史学理论研究, 2007 (4) :34-41.
[23] 贺璋��。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浅探[J].学术研究, 2004 (9) :88-93.
[24] 宋立宏, 王艳。从“自我教化”到同化:近代柏林的沙龙犹太妇女[J].学海, 2012 (5) .
[25]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66-70.
[26] 李沁叶。文化消解、身份困惑与身份特征的再造--论《忽至森林深处》中犹太人的文化身份问题[J].社科纵横, 2014 (8) :139-142.
[27] 徐新。犹太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8] Jacob KATZ. German Culture and the Jews[J]. Arbitrium, 1987 (3) :85-99.
[29]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337.
[30] 查姆·伯曼特。犹太人[M].冯玮,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240.
[31] 钟志清。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J].西亚非洲, 2015 (6) :20-35.
[32] 李宗陶。诺贝尔提名作家奥兹讲述好人之间的战争[J].南方人物周刊, 2007 (23) :63-65.
[33] 郑丽。生活乃是对话--阿摩司·奥兹《等待》中的对话哲学[J].外国文学, 2010 (2) :3-9.
[34] 阿摩司·奥兹。费玛[M].范一泓,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183.
[35] 惠雁冰。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J].人文杂志, 2007 (4) :11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