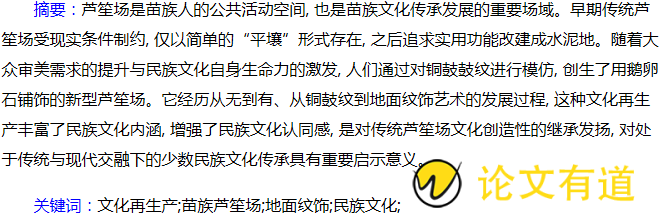
芦笙场是苗族人民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牯藏节、芦笙会等重大节庆聚会皆在此举行, 闲暇娱乐、对歌寻偶也在此开展。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贵州省苗族人口为96.8万人, 约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1%, 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自治州, 松桃、印江、威宁等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黔东南州) 达0万, 成为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1]因此, 将黔东南州作为苗族芦笙场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芦笙场也叫芦笙堂、月场或芦笙坪, 关于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原始氏族时代祭祀祖神或祝颂之类的宗教集会, 各种宗教集会, 给芦笙场的形成提供了时机、场合和条件……他们在希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时候, 便聚而舞蹈歌唱, 以歌舞娱神, 祈求神灵暗中保佑, 消灾降福。”[]所以祭祀是芦笙场的重要功能之一, 至今在苗族十三年一次的牯藏节中, 芦笙场仍然是核心的祭祀场所。与此同时, 芦笙场还有集会和婚配的功能。在农闲时节, 各大芦笙场轮流举行看会活动, 例如跳芦笙舞、吹芦笙、斗牛等。看会的芦笙场也为青年男女搭建了相识沟通的平台, 清代有文字记载:“预择平壤为月场, 及期, 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面前, 女振铃继之于后以为节, 并肩舞蹈, 回翔婉转, 终日不倦。”[]凯里舟溪镇甘囊香芦笙堂19年的立碑也云:“窃维吹笙跳月, 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正当娱乐……更为我苗族自由婚配佳期。”看会期间很多男女青年在笙歌合舞中相悦认识结为连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快速发展, 芦笙场在集会场所的基础上增加了民族文化展演的新功能。

民族地区日益发展与开放, 外界对少数民族不论是出于猎奇旅游还是文化旅游的庞大市场需求促使了芦笙场向装饰性、审美性方向转变, 同时也是地方相关部门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重要媒介。芦笙场从“平壤”、河滩或者水泥地成功转型为由鹅卵石铺饰成铜鼓鼓纹、有圆心的广场, 甚至有些芦笙场中央树立苗族石刻的图腾柱, 这不仅是对审美和实用的价值追求, 更是苗族文化顺应新时代的文化再生产。在继承发扬马克思的相关学说中,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最为代表。布迪厄将资本按基本形态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最早是作为教育领域的理论假定“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 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 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指“再制造、繁育、复制、再现。”[5]布迪厄“把‘文化资本’与‘再生产’结合起来, 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的理论。”[6]文化领域与教育领域具有同构性, 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指标来衡量, 通过已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民族文化传承更应引起关注。
一、已有文化资本:传统芦笙场
传统芦笙场指尚未发展到有地面纹饰的芦笙场。芦笙场从静态平面化视角来看它主要是用于跳芦笙的广场, 我们更应该从动态立体的角度把芦笙场看作是人、物、时空有机融合的场域, 其中物包括有形的芦笙、铜鼓、图腾柱, 无形的芦笙旋律、铜鼓声、歌声等等, 所有因素在同一个空间交汇, 形成具有凝聚性的苗族文化特殊空间场域 (field)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7]传统芦笙场的场域中在看会活动中主要的客观关系网络如下图所示: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状态, 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客观的状态, 以文化商品的形式;体制的状态, 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8]在作为已有文化资本的传统芦笙场中主要以前两种形式存在:首先是最核心的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具体状态。这是一种抽象不可估量的关于自我民族文化的精神,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民族认同感。在外界力量介入之前, 围绕芦笙场的各种活动基本遵从苗族民间自组织原则规律地、持续地开展, 或祭祀娱神, 或通过集会为不同地区的同胞提供文化、感情上的交流。同时芦笙会还可以无形中促进人的社会化。文化资本的第二种重要形式是客观的状态, 在传统的芦笙场场域中客观化的“文化商品”主要包含乐器方面有铜鼓、芦笙, 以及精美的苗族服饰。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 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刺激了传统芦笙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二、芦笙场地面纹饰:文化再生产的结果
(一) 从无到有
清代则以“平壤为月场”, 上个世纪末芦笙场所在地“一般是离村寨不远的草坪、坡地、河坝或其它空旷的郊野, 晚上有的则临时转移至村口或寨内。”[9]调查发现:如今旁海镇的芦笙场在江边空旷的河坝;舟溪甘囊香芦笙场是由曾经的河坝改造而来;丹寨县南皋乡芦笙场也是山间平地。黔东南州芦笙场在重新修缮之前一般为泥地或河边沙滩, 条件较好者也只是水泥地。苗族芦笙场最初选址除了满足巫师占卜要求外就是足够平坦宽广, 容纳可能参与芦笙场集会的人们, 关注重在人的活动而缺乏对芦笙场的地面进行装饰。
新世纪以凯里巴拉河畔郎德苗寨与南花苗寨的先后兴起揭开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快速发展新时期。郎德与南花都拥有各自的芦笙场, 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 苗寨芦笙场都经过相应修葺美化:郎德芦笙场铺有鹅卵石, 南花芦笙场和西江芦笙场中央树立了石柱牛角的图腾, 芦笙场进入关注地面纹饰审美的时代。
(二) 从铜鼓纹到地面纹饰
郎德苗寨是黔东南州旅游开发的第一个苗寨, 1985年作为黔东南民族风情旅游点率先对外开放, 199年载入《中国博物馆志》, 199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为考察苗族文化、领略苗族风情的首选村寨, 有效地刺激了民族文化的再生产:位于寨子中心的芦笙场是黔东南州最早被改造修葺, 该芦笙场呈圆形, 铺满整齐规则的鹅卵石, 场地中心由鹅卵石铺成太阳纹标志, 有十二道太阳光芒, 周围还有飞奔的骏马图案。黔东南重建的芦笙场外围的细晕纹饰各不相同, 但中心都拥有明显的太阳纹符号。太阳纹作为芦笙场的地面中心纹饰得到极大推广是因为该符号所附的铜鼓本身就是苗族的重要文化器物。
传说铜鼓是“天王”赐给补天有功的始祖薅妮。在苗族族群里, 铜鼓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也是祖先神灵的寄托之所。黔东南州的铜鼓据出土地被命名为“麻江式”。“麻江式”铜鼓“流行年代的上限可到南宋, 谷峒鼓出土于宋明之际的墓中, 也可说明这一点。”[10]“铜鼓主要保存在贵州苗族之中, 居住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的苗族, 至今使用铜鼓最为普遍。”[11]在节会的芦笙场中央, 由寨老敲击铜鼓, 另一人提助音桶在铜鼓背后一开一合, 通过共鸣增大铜鼓的声音, 同时变换节奏。铜鼓声与芦笙合奏, 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根据旋律改变舞步。雷山牯藏节还有一整套从“起鼓”到“还鼓”的铜鼓崇拜仪式。铜鼓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而且在精神层面受到高度崇拜, 已然成为苗族文化中权力的符号。
铜鼓表面有很多装饰性的纹路:太阳纹、云雷纹、游旗纹、钱纹等等, 太阳纹在敲击的中心, 也最为明显, 所以有人称铜鼓为“太阳鼓”。根据铜鼓修建的广场也有的直接命名为“铜鼓广场”。在芦笙场的地面纹饰中, 保留铜鼓的太阳纹和细晕, 外形也如铜鼓为圆形。俯瞰芦笙场, 犹如平置在大地的铜鼓。铜鼓纹从鼓面走到地面, 既是巧合也是文化再生产的必然, 人们智慧地利用清水江边的鹅卵石, 巧妙地从外形到纹饰还原铜鼓的物像, 符合人们对苗族文化的审美期待。铜鼓原本是鼓社头才有资格保存的器物, 通过芦笙场地面装饰对它的模仿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古老的符号在新时代结合芦笙场得到的再生产, 体现了苗族文化强大生命力。
(三) 从特殊到普遍性的地面装饰艺术
特殊性属偶然, 由偶然发展到普遍性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最初对芦笙场地面进行装饰改造的区域仅限于旅游开发的苗族村寨。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新型芦笙场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甚至已经作为各类广场的基本形式:雷山县、台江县、剑河县等苗族聚居地都有模仿芦笙场建造的休闲广场, 而且芦笙和铜鼓的雕塑比比皆是。据统计, 凯里市下属村镇可用于举行集会活动的芦笙场就有个。芦笙场模仿、还原铜鼓形态对于最早进行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是文化再生产的特殊事件, 它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到人们广泛认可并不自觉地模仿、成为特色的民族文化景观, 说明有地面纹饰的芦笙场已然成为苗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过去跳芦笙的地方称作芦笙场, 现在是在芦笙场上跳芦笙舞, 印证了人创造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 这种与芦笙场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苗族人们生活的惯习 (habitus) , 它“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 它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 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物。”[1]
具有铜鼓纹装饰的芦笙场之所以具有如此影响力, 与铜鼓和传统芦笙场的功能密不可分。铜鼓在苗族祭祀、丧葬和重大节庆活动中发挥着礼器作用, 可以感召远祖赐予族群同胞精神力量, 也可以通过铜鼓将亡灵护送到达祖先存在的“远方”。在此意义上铜鼓已经升华为一种具有民族认同感召力的“圣物”而非现实层面物品。同时, 芦笙场也是由寨老通过烧香占卜等特殊方式选址找到可以和神灵沟通祭祀的地方。因此, 铜鼓和芦笙场除了现实中提供音乐节奏与空间场地外还有更深的象征意义:身着盛装的人们在铜鼓与芦笙伴奏下翩翩起舞, 既是集体娱乐活动, 更是通过在“人、铜鼓、芦笙、芦笙场”构建的民族文化场域中与神和远祖沟通的特殊方式。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黔东南州苗族地区同其他城市一样开展现代化建设, 但是在苗族同胞灵魂深处依然存在着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方式, 所以才会出现近些年各种形制芦笙场在城市文明中快速播散且化为苗族文化的一部分。
三、民族文化资本积累:文化再生产的价值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以人类文化为依据“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1]。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劳作”创造符号。创造符号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动物只能拥有“信号”。符号作为人类文化精神与物质层面的媒介, 它作为精神的表象与物质的证实, 能独立于人的存在得到不断的累积继承与发展。铜鼓自身作为苗族文化历史创造出来的特殊符号,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们“择其善者”地将鼓面纹路再生产到芦笙场的地面装饰, 通过符号创生新的“芦笙场符号”, 这显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关于文化本身的内涵,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叙述:“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 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1]鼓纹符号迁移至地面实现文化再生产进而形成新的芦笙场符号, 对苗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和价值。
(一) 丰富民族文化内涵
芦笙场的地面装饰从无到有, 从“平壤”到鹅卵石铺饰的铜鼓纹饰, 通过文化再生产, 丰富了传统芦笙场文化的环境创设。同时在民族舞蹈方面, 芦笙场地面的铜鼓纹饰与传统苗族集体舞达到了内在审美的高度统一。苗族集体芦笙舞的运动路线是以铜鼓为中心围圈而舞, 铜鼓放置在芦笙场的太阳纹处, 外层是青壮年男子吹笙队伍, 身着苗装的女子紧跟吹笙男子, 最外圈则是游客、老人或小孩。所有的人随着铜鼓芦笙和谐的旋律、伴着统一的步伐不断前进、起舞, 加入的人越多, 舞圈越大。圈状的舞蹈队伍好比鼓纹上的晕线, 铜鼓、芦笙、旋律、舞步、服饰等特文化物象构成苗族整体的符号。
对于苗族的集体舞蹈艺术来说, 圆圈状是它的主要舞蹈形态。圆圈与铜鼓的鼓面相似, 既象征着太阳, 也是生命的轮回, 还有团圆美满的意蕴, 体现着苗族人朴素的哲学观念。圆圈舞也是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中共有的舞蹈形式。例如藏族的“锅庄舞”、彝族的“达体舞”、鄂温克的“舞火舞”等都是以圆圈的形式展现。从客观上讲, 苗族的芦笙舞与其居住地缺乏开阔的表演场地开阔有密切联系, 由于空间相对狭窄, 无法容纳太复杂的队形, “围圈而舞既可以节省空间, 又可以使舞蹈无限循环的进行。为了便于集体的向心性团聚;为了在狭小的空间里寻求周流不息的运动, 为了创造一种流畅的审美风格。”[15]这种“流畅的审美风格”与芦笙场的地面纹饰得到高度契合和交相辉映, 丰富了芦笙场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 经过修饰的芦笙场也成为苗族村寨里的新景观。有的芦笙场边缘还修建了风雨廊, 为人们提供休憩之所。休闲时, 妇女们在风雨廊聚集刺绣、交流生活日常, 孩子们在芦笙场上追逐嬉戏, 形成了苗寨和谐的闲暇文化。
(二)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当今经济高速发展、媒介的高度发达给相对传统保守的民族文化强大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 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尤为重要。“所谓的民族认同实际上便是找准独特的民族精神, 这种独特的精神就民族来说就如同一个人的独特性……所有文化, 总是在其漫漫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因其所处的天地系统的独特性以及其民族与这一独特的天地系统的独特相互作用方式形成的。”[16]苗族在与其它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保留了自己的口头语言、信仰崇拜、艺术形式和民风民俗。牯藏节祭祀是血缘性的, 参与者为同一宗族。而芦笙会则呈现出地缘性特点。参与芦笙会的人往往来自不同宗系, 他们在芦笙场中参与民族共同的节庆活动, 在集体的芦笙舞中手拉手围成圈状共同绕着中心舞蹈, 步伐和舞姿协调统一, 个体融入到集体中, 这种向心力教人团结协作时也给人以安全感。
芦笙场从有形上来说是苗族人集会沟通的公共空间, 从无形上看开展各种民族活动的芦笙场是增强苗族人之间凝聚力的重要平台, 铜鼓、芦笙、银饰等各种苗族文化的物象在舞蹈音律的融合下构成一个特别的芦笙场文化的场域, 人们在这个场域中感受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心理。芦笙场的地面纹饰与鼓纹和谐统一, 它再次强调铜鼓是权力象征、是苗族文化的代表器物, 增加了“场”吸引力。当今社会快速发展, 苗乡日益开放, 与时俱进的同时更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在旅游发展推手下形成的新时期鹅卵石铺饰芦笙场是苗族聚居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共同铸造, 是历史发展中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它强化了生活在这一独特天地系统的苗族人的文化符号, 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三) 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芦笙场曾经是“离村寨不远的草坪、坡地、河坝或其它空旷的郊野”, 大家约定俗成。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芦笙场很容易遭到占用、自然破坏。新时期经过修葺的芦笙场平坦美观、有地面纹饰, 弧形的风雨廊为芦笙场确定固定边界, 各个时段的民族活动都可以如期进行, 为传承民族文化提供富含民族文化底蕴的公共空间。
其次, 铜鼓的鼓纹从鼓面走到地面, 给我们展示了一条传承民族文化的可行道路:民族文化再生产。传承民族文化不是以怜悯者的眼光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简单地保护, 而是要发现该文化内部具有生命力的能量并激发它, 通过文化再造将自我的文化转化为发展的力量, 变“输血式”为“造血式”的发展。新时期芦笙场地面纹饰的变化就是典型案例, 第一个拥有鹅卵石铺饰的鼓纹芦笙场是偶然, 当新型芦笙场二十年左右几乎遍布黔东南州苗族聚居区受到人们的认可并转化为当地的文化景观, 这就是历史选择。所以传承民族文化应找准某一方面的核心文化器物, 并发掘与它有高度契合性的物品, 与时俱进开展创新, 在不断摸索中发现民族文化创生点。
再次, 芦笙场的地面纹饰作为符号更容易得到传承。符号由人创造且可以脱离创造者而存在, 这是它更易积累、传承的重要因素。传统的芦笙场没有地面装饰要素, 仅作为集会约定俗成的公共空间, 它的意义随集会结束而淡化。新时期芦笙场的地面纹饰以不同颜色形状的鹅卵石直接模仿铜鼓纹, 逐渐形成了与鼓纹相似的符号特征。具备符号特征的芦笙场文化可以脱离集会人群独立存在, 与传统的芦笙场相比较更容易跨越时空的局限得到积淀和传承。
结语
“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 始终都是同人的生存需要, 同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的生存的意向紧密地相联系的……人的精神生命的超越性, 一方面使人的生存能力本身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力;另一方面, 又使人的生存意向, 始终朝着新的可能的超越层次发展。”[17]黔东南州作为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 同时铜鼓的使用又主要分布在该州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的苗族中, 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铜鼓作为苗族礼器成为芦笙场文化发展的内在创生点, 鼓纹从鼓面迁移到地面并逐渐凝练成为芦笙场文化的符号象征, 这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 有效达成了对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扬。这一事实启发我们在民族文化保护和继承方面, 积极面对区域开发、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等等复杂因素, 可以将这些外来冲击力经过本土文化的再生产转化为民族自身发展动力, 真正具有生命原动力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多力场中能够找到平衡点, 最终实现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情情况 (2017-09-29) [2018-03-23]
[2]杨昌鸟国.试论苗族“芦笙场文化”[J].贵州社会科学, 1987 (10) :10-15.
[3] (清) 田雯编, 罗书勤等点校.黔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20.
[4] (法) 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93.
[5]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1678.
[6]余秀兰.文化再生产: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6 (2) :18-26.
[7] (法) 皮埃尔·布迪厄; (美)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 李康,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4.
[8] (法) 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92-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