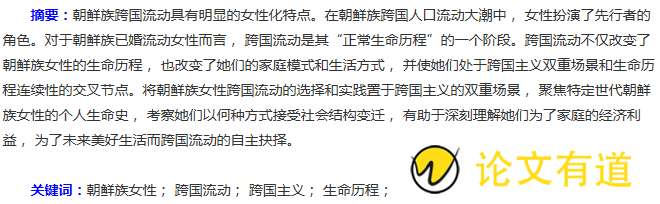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深刻影响了主要聚居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社会。朝鲜族不仅开始在国内沿海城市流动, 而且开始向国外流动, 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 朝鲜族向韩国流动的人数逐年递增。 (1) 截止2017年11月, 在韩朝鲜族人数达677 212人。 (2) 也就是说, 约占朝鲜族总人口 (约183万) 37%左右的朝鲜族人口正在韩国工作和生活, 与此同时中国朝鲜族也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族裔群体”[1].

朝鲜族人口流动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并引起学界关注。对此, 中国学界主要聚焦人口流动对朝鲜族社会的影响、朝鲜族在跨国流动中的认同及其跨国网络。韩国学界主要关注朝鲜族在韩国的社会文化适应、人口流动对朝鲜族共同体的影响、朝鲜族跨国网络的形成及其功能。这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以朝鲜族流动女性为中心的研究成果。事实上, 自朝鲜族跨国流动伊始, 朝鲜族女性就“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2],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成为流动大潮的主力军。需要指出的是, 朝鲜族女性的流动已由传统的“依附移民”转变为“自主移民”.[3]据韩国法务部外国人登录统计, 朝鲜族女性一直占朝鲜族流动总人数的50%左右。对此,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朝鲜族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及其对朝鲜族社会的影响。相对而言, 韩国学者比较关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在韩国社会的适应及朝鲜族“流动的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 ”现象, 特别是关于后者的研究超越了单纯关注女性经验的层次, 将其流动置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背景中, 深入考察朝鲜族女性在跨国流动的生活经验和身份变迁, 指出朝鲜族女性虽然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弱化了母亲身份, 强化了“性别化个人”身份, 但流动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缺席”是实现家庭“生计维持和改善”的前提和手段。[4]伴随2007年韩国政府颁行访问就业制, 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更加便利, 朝鲜族流动女性更能积极发挥“远距离母性”[5]功能。
不过, 关于朝鲜族流动女性的现有研究虽然从行为者视角揭示了她们的个体流动经验, 但对理解其身处跨国主义场景中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的解释还不够充分。的确, 朝鲜族流动女性从各自情况出发, 积极主动地选择了流动, 但她们作为跨国流动者毕竟只能以“少数者”和“流动者”的身份在两个以上的空间生活, 她们的流动在多重空间 (流出地和流入地) 和多重时间 (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交错重叠。从这一点来看, 现有研究并没有充分揭示朝鲜族流动女性是如何在持续的双重性和偶尔的冲突性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为此, 本文拟从跨国主义和生命历程的视野, 把朝鲜族女性跨国流动的选择和实践置于跨国主义的双重场景或空间中, 以强调性别、空间和时间、生命历程对理解朝鲜族女性跨国流动体验的重要性。
本文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通过深层访谈收集的个人口述生命史。笔者曾于2014年5月至9月在韩国和50多位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女性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 本文的分析资料节选了其中的口述史资料。
二、研究视角:跨国主义和生命历程
所谓跨国主义, 即离开一个地方的移民者到另一个地方成为定居者后, 千方百计地试图把流出地和流入地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 进而形成与维系连接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多维社会关系的进程。跨国主义视角注重流动者的跨界性 (cross-border) , 强调流动者的生活取决于跨国社会场景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美国学者Linda Basch、Nina Glick Schiller和Cristina Szanton Blanc较早提出跨国主义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她们认为, 所谓跨国主义, 是移民建立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景 (social fields) 的社会过程。跨国移民 (trans-migrants) , 是建立和维持跨界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多重联系的群体, 他们借由多重的联系抵御或回应流动过程中面临的困难。移民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多重参与, 是跨国主义的核心要素。[6]由于移民在流出国和流入国的多重参与 (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是以移民建立的网络关系为基础, 所以跨国社会网络对跨国移民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 Alejandro Portes等学者主张, 跨国移民研究应以移民个人及其支持网络为单位。[7]后来, Faist又把跨国社会场景发展为跨国社会空间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 将移民体系视为打破边界的过程, 在新的社会空间里, 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是构成其中的一部分。[8]
过去, 当我们谈到离散的时候往往认为, 离散者处于既不属于母国 (想象的共同体) , 也不属于定居国的边缘地位, 但现在跨国流动者处于“属于任一地方”的跨国网络之中, 他们并没有处于强制性离散造成的悲惨生活中, 也没有从流出地连根拔起, 相反和流出地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流入地不再是流动者的唯一据点 (base) , 而是暂时中转站 (points of passage or way stations) .[9]最近也有经验研究表明, 对于跨国流动者而言, “四海为家”是有可能的。跨国流动者之所以能够“扎根四海”, 是因为民族认同在持续发挥作用的同时, 流动的生活、多场域的特殊经历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 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离开落后的流出地 (发展中国家) 的流动者发现, 跨国移民让他们享受到了流入地 (发达国家) 的各种好处, 而其中的一些好处他们以汇款形式送给留在家乡的亲属。他们虽然离开家乡, 但他们的流动却给流出地带来变化, 而他们也对流入地也不无眷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多数人及其后裔和流出地的关系渐行渐远, 他们开始重新适应流入地这一新的环境, 并将眷恋和承诺倾注到自己实际生活的地方。[11]
朝鲜族的韩国行是否属于“离散与回归”?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从聚焦行动者的跨国主义视角, 从一个民族持续离散的历史而言, 对考察“作为离散者的同胞”和“作为流动者的外国人”之间微妙关系而言, 朝鲜族向韩国的跨国流动是绝佳的个案。当然, 当代朝鲜族韩国流动并不存在强制性的离散经验, 大部分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以劳务输出为主, 不过与在韩务工的其他外国流动者不同的是, 他们要面对更多样化的冲突和困境。就此而言, 关注场景的双重性或连接性的跨国主义视角, 有助于理解当代朝鲜族跨国流动。另外, 从跨国流动的经验研究来看, 与其说流动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离开家乡的“事实”, 倒不如说他们视流动为其漫长生命历程的“一时”行为。[9]35-49他们之所以接受流动带来的家庭分离, 是因为相信并期待有朝一日再次相聚。当然他们也明白这种期待不会轻易实现, 他们只是相信这种流动生活是暂时的, 而这意味着他们将流动和生命历程密切联系起来。
生命历程是将社会变迁及其发生的历时性时空与身处其中的个人生命史联系起来的理论和视角, 把生活经验发生重大变化的个人史置于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考察 (contextualist perspective) .特定社会变迁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置身于特定社会变迁的时间和空间的个人生活, 而个人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或回应则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具体内容。[12]基于结构和行为这种双向关系认识的生命历程视角特别关注特定同期组群 (cohort) 的共有经验, 将拥有相同历史经验的同期组群如何以独特方式回应社会变迁为主要分析对象, 而不是个别化的个人。在这里, 个人不再是“自我行为者” (biographical actors) [13]10, 或绝对遵守社会规范的顺从者, 或追求主观能动性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 而是拥有时间性的自我主导型的行为者。在理解个人对社会结构的反应方面, 关键要素是个人生命史。个人生命史常常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是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个人面对社会变迁时, 都会做出不同的回应、不同的选择。通常情况下, 个人尽管面对社会结构变化, 但其长久形成的惯习和态度却有保持不变的趋势。[13]11个体面对生命历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都会迅速做出回应, 同时相信这种变化的“暂时性”.在跨国流动过程中, 流动更容易被视为“暂时的生命过程”.当然, 根据世代、性别、阶层的不同, 个人对流动在其生命历程中的意义和流动的“暂时性”程度会有所不同。鉴于此, 本文聚焦朝鲜族跨国流动女性的个人生命史, 特别是朝鲜族女性流动前后具体生活实践的差异和冲突, 来考察她们作为行动主体介入跨国流动的过程和结果, 通过流动者的空间“在场”和“不在场”的关联性 (即空间双重性) 及其与流动者生命历程 (life course) 之间的交错, 考察她们以何种方式接受社会变迁, 如何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 如何为了家庭的经济利益, 为了“未来美好生活”而做出跨国流动的自主抉择。
三、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朝鲜族女性生命历程的社会结构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政策。就流动而言, 最大的变化是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户籍制度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不仅规范了迁移、流动, 而且也衍生了城市优先、农村靠后的城乡二元社会, 户口成为控制迁移的有效工具。1984年10月, 国务院允许在小城镇工作的农民办理“自理粮”户口, 这标志着城乡之间的严格界线开始松动。1985年, 公安部出台针对迁移人口的暂住证政策。1995年后, 中国开始全面发行临时居住证。这些政策规定, 加上粮食、住房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逐步市场化, 使得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容易。[14]这样一来, 中国的城市人口急速增长, 而农村人口开始相应减少。据统计, 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 增加到1984年的23.1%, 1992年的27.63%, 2003年的40.53%.[15]事实上, 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远远超过了官方统计数据。
这样, 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 寻求经济利益的冲动使中国的流动人口与日俱增, 而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被访者的生命过程。她们亲眼目睹并体验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 从而有机会走上与其父辈甚至祖辈完全不同的道路。Y某 (1966年生, 农民, 初中毕业, 来韩国10年, 在饭店跑堂, 有子女1名) 发现, 自己完全有希望过上与其父母不同的生活, 再也不用死守在一个地方。对朝鲜族女性而言, 和其他途径或手段相比, 流动即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 更容易实现她们所期待的未来。由此, 通过流动改变生活开始被视为“正常的生命历程”而被接受下来, 而所有的这些可能性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市场经济, “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 打破了一直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16].对于Z某 (1965年生, 高中毕业, 企业工人, 来韩国8年, 在饭店跑堂, 有子女1名) 来说, 韩国行是新的生活机会的前提, 是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 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 不仅改变了朝鲜族社会, 而且也改变了朝鲜族个体的“正常生活”.在此之前, 大多数被访者虽然接受了中等甚至高等教育, 但是她们很少设想过离开朝鲜族聚居地, 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朝鲜族女性来说, 除非是考上大学、参军或者被招工, 摆脱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朝鲜族农村妇女来说, 除了极少部分女性在大学毕业后能到城里工作, 大部分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被访者大都表示, 她们从小就视生产劳动为理所当然之事, 当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她们需要承担的劳动责任在程度上多少有所不同。大多数朝鲜族女性的生活基本上以结婚为明显的分界线:在婚前, 基本上不需要担心家庭生计问题, 而在婚后, 除了生育和抚育子女外, 她们还要承担家庭生计。
现有研究及访谈结果都显示, 与汉族相比, 朝鲜族社会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更明显。除了生产劳动之外, 朝鲜族女性还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 这一点与中国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 人们常用“妇女能顶半边天”来比喻女性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强调男女平等, 强调女性社会地位的同时, 在集体生产中也强调不论性别都要平等地参加劳动。这样, 朝鲜族女性在婚后一直承担生产和生育双重劳动。至于城里的职业女性, 虽然大多拥有稳定的工作, 子女由单位托儿所照看, 或者交给婆家或娘家父母照顾, 但她们也表示国内的生活比起在韩国的务工生活更沉重。被访者H某 (1958年生, 中专毕业, 来韩国20年, 在市场卖服装, 有子女2名) 说, “我和公婆一起住, 家里小叔子小姑子都没结婚, 也一起住。用钱的地方特别多。我在书店上班, 从早上8点上班, 到晚上5点, 一直在书店卖书。周末, 把店里的书拿到乡下去卖, 然后在农村买蜂蜜啊, 木耳啊, 山野菜啥的, 再弄到市场去卖。那么远的路, 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来回。当时也不知道胆子怎么那么大。我丈夫从来不做这种活。有的时候, 为了赶路, 早晨三、四点从家走, 晚上半夜到家, 舀一瓢缸里的水, 没等喝完, 就瘫倒在炕上了。”相反, 大部分农村女性由于和亲戚 (娘家, 特别是婆家) 住在一个村里, 很多家务工作可以在家族内部得到分担。但无论如何, 朝鲜族已婚女性都要扮演生产和生育的双重角色。如果说职业女性的经济生活还算相对稳定的话, 那么农村女性在承担艰苦繁重的劳作同时, 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带来的子女教育机会匮乏和学费等剧增的经济负担。这样, 生活在落后农村的朝鲜族女性很快就意识到向城市 (1) 、向外国 (主要是韩国) 流动的必要性。而对于那些在来韩国之前有基本经济保障的城市职业女性来说, 她们最终也意识到流动的重要性, 特别是如果丈夫职业不稳定 (如工厂倒闭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 、自己面临退休 (当时大部分单位的女性正式退休年龄是50周岁) , 韩国行就成为她们生命某个阶段中的最佳机会。当然, 她们也知晓韩国行意味着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 而且她们也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在韩国劳动的恶劣环境和被歧视的差别待遇, 但这并不能阻挡她们流动的渴望。能够赚到比在中国高出六、七倍工资的事实, 即便对职业女性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Z某、H某) .
朝鲜族流动女性在韩国大多从事饭店、清洁、看护等服务行业的3D工种, 是韩国劳务市场的低廉劳动力, 尽管如此, 她们比起朝鲜族男性工作机会更多, 收入也更稳定, 更能攒下钱, 所以对于朝鲜族家庭来说, 女性外出流动是反复权衡后的最佳选择。到有赚钱机会的地方打工不仅对朝鲜族家庭是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而且对已婚朝鲜族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是在“明知”无法照顾子女的后果的情况下还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J某, 1963年生, 大专毕业, 来韩国11年, 在医院做看护, 有子女1名) .既然劳动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避免, 那么在哪里赚钱、能赚多少钱就比起劳动强度更重要了。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 “反正都是受累, 那还不如干能赚更多钱的活”.另外, 对于一直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的同时还要从事生产劳动的朝鲜族女性来说, 流动不仅是实现生产劳动的责任而无法回避的选择, 也是从繁重的双重劳动 (生产劳动和生育劳动) 获得“解放”的机会。正如X某 (1961年生, 初中毕业, 农民, 来韩国11年, 在饭店后厨打工, 有子女2名) 所说, “在韩国饭店打工, 和农活比起来啥都不是”.
研究表明, 婚恋经历、对婚姻期望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固着, 是影响妇女流动的重要因素, 而流动经历又会反作用于妇女的婚姻观念。[17]在传统朝鲜族家庭中, 妇女处于绝对从属地位, 主要负责生育子女和服务家族。但自改革开放以来, 朝鲜族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加强, 加上她们普遍具有坚毅果敢和头脑灵活的特点, 从而在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在决定跨国流动到韩国务工的选择过程中, 子女教育问题、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家庭婚姻生活的烦恼和矛盾相结合, 成为朝鲜族女性跨国流动的驱动力。被访者L某 (1970年生, 大学毕业, 来韩国8年, 在饭店打工, 有子女1名) 这样告诉笔者, “我是因为想摆脱丈夫才来韩国的, 我丈夫酒品不好。和他在一起, 我什么话都不敢说。趁着都来韩国打工, 我也出来了。我来这里, 就是希望找到合心意的人”.
可见, 流动不仅成为朝鲜族女性主动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 而且也是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获得个人现代化的过程。如果说朝鲜族作为跨境移民, 他们的第一代向韩国流动是以血缘和母国为中心的“回归”, 那么他们的第二、三代甚至第四代是以特定生命阶段的目标为中心的流动, 前者更具政治性和历史性, 而后者与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变迁以及他们独特的个人生命史密切相关。[18]通过流动, 长期承担生产和生育双重劳动的朝鲜族已婚女性进入了集中生产劳动这一角色的生命阶段。
四、跨国流动与未来机会:朝鲜族女性生命历程的生活结构变迁
大多数被访者在韩国从事保姆、在旅馆当清洁工、在饭店后厨帮工和跑堂、在服装厂打工等各种低层次的职种。从被访者当时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流动时间较长, 收入比较稳定, 生活也趋向安定。当然她们也都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在流动初期不堪回首的阶段。到韩国打工的前提, 就是保证长时间劳动。以在饭店做月薪制工作的被访者为例, 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 (从上午10点到下午10点) .月薪制的工作虽然劳动时间长, 但好处是可以偶尔休息, 而且在一个地方的长时间工作也可以成为她们应聘新工作的资历。不过也有人选择到派出部 (职业介绍所) 做日薪工, 特别是在2007年访问就业制以前通过探亲研修等来韩国, 在超过规定的滞留时间留下来打工的朝鲜族“非法滞留者”的身份更愿意选择日薪工作。总之, 作为从事低收入、长时间劳动的朝鲜族流动女性, 她们对月薪制和日薪制工作的优缺点都有直接的体验, 通常选择更有利于自己实际情况的工作。
那么, 朝鲜族流动女性是怎样熬过这种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呢?当然, 赚到相当于中国工资好几倍的钱是根本动力。从被访者的口述可以发现, 她们一方面厌倦长时间劳动, 但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生活的重心。对她们来说, 在韩国的“长时间劳动经验”是平生第一次经历。虽然工资高, 但要忍受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事实, 这和过去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经验多少是矛盾的。不过, 在韩国每天赚到的钱除了必须开销之后还有剩余,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们的消费欲。Q某 (1973年生, 师范学校毕业, 来韩国7年, 旅馆做清洁工, 有子女1名) 说, “韩国人都说中国物价便宜, 但是如果按中国的工资来看, 那物价就相当高了。韩国的东西你算成人民币是贵, 但是要按韩国的工资收入比的话, 那还是便宜。在这里, 一天打工赚的钱怎么也够你吃几天的, 最主要的是, 每个月还能往银行存不少钱”.
另外, 朝鲜族女性通过在中国社会接受男女平等观念、很早就参加社会工作的经验, 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后率先跳入商海的经验, 使得她们在“韩国梦”的驱动下跨国流动的过程中,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生活的姿态和强韧的女性特质。J某说, 朝鲜族女性身上有来自先辈从朝鲜半岛“冒禁潜耕求生计”的跨国移民 (离散) 经验以及她们自己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经验所刻下的烙印。“我们想比别人活得好, 想比别人赚更多钱的欲望可能更强……我们这一代女性很早就出来工作了。在社会主义国家, 男女平等, 女人和男人一样, 堂堂正正……来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女性都不是一般人。”这样, 被访者在内化韩国的长时间劳动节奏过程中, 将“努力劳动”和“有钱”联系起来, 将“努力劳动”视为“有钱”的捷径 (G某) , 而且认为能干活、有活干也是一种“福气” (Y某) .
有研究认为, 朝鲜族流动女性被迅速编入韩国劳动力市场底层, 在低端行业从事高弹性工作, 弥补了韩国某些行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19], 这是因为她们具有被编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动机。当然,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 她们被编入的动机并不是在现在的韩国成就什么, 而是在未来的中国成就什么。从现有研究和笔者访谈过程中发现, 维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是朝鲜族为了赚钱而走上跨国流动之旅的背后推动力, 她们的跨国之旅“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计问题, 而是一种为了进一步提高其生活质量, 把经济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 最终实现整个家庭社会地位和身份上升的策略”[20].朝鲜族已婚女性为了未来美好生活而忍受现在的辛苦劳动, 这是因为她们认为在未来的计划中她们就算不能通过自己的生活, 也能通过子女的生活回到“现在”.
大部分被访者非常热衷于在中国国内城市买房子, 这一点和她们相信通过子女回归中国的生活循环有关, 也是她们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和身份的重要实践。当然我们也不否认, 在城里买房子可能是出于投资动机, 但从被访者口述生命史来看, 在城里买房还具有不同于投资的象征意味。房子, 作为保障回归中国的据点, 不仅是她们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身份确认, 而且也是评价流动女性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准。另据其他相关经验研究, 买房子, 也是朝鲜族社会“评价一个婚姻移民家族女儿在韩国的婚嫁如何, 是否孝顺父母, 娘家人出国打工是否成功等多方面的公认的标准”[2].对于朝鲜族已婚流动女性而言, 买房子不仅体现了她们对子女的期待, 而且也是保障自己未来老年生活的投资。
与此同时, 她们对子女将来的职业和定居地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大部分被访者表示, 她们虽然也希望子女的未来能够在韩国成就, 但期待并相信朝鲜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被访者H某说:“以后, 也是中国会更有发展, 更有希望, 在这里过得好, 也是暂时的。目前我们在韩国还有一点赚钱的机会, 但是现在韩国人的企业都往中国跑, 所以, 从长远来看, 在中国发展会更有前途。”可见, 朝鲜族已婚流动女性并不关心自己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而是期待着以中国朝鲜族的现在生活为基准的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并为接下来的生命阶段做准备, 而这也充分体现了跨国主义的“虽然流动但却没有离开”、虽然跨越国家边界但却反复重构边界的跨国生活的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 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是朝鲜族得以跨国流动的契机, 这在朝鲜族摆脱束缚在特定空间工作和生活、改变其社会阶层和地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 对于朝鲜族而言, 韩国行被视为实现美好生活和未来希望的捷径并逐渐日常生活化。对于朝鲜族已婚流动女性而言, 她们的生命历程在结婚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婚前, 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社会主义体制变化, 但她们并没有期待自己的生命历程会发生变化;婚后, 她们不仅扮演家庭生计承担者的角色, 而且渐渐接受了流动是为了家庭生计和抚养子女的暂时生命历程, 这是因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内化了自己作为主要的生育和生计承担者的双重角色。事实上, 不少被访者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双重角色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压力心有余悸, 而对于流动到韩国进而摆脱这种双重角色多少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她们作为在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者, 特别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劳动者, 在忍受高强度长时间劳动的过程中, 一方面将其视为通往未来新生活的捷径, 另一方面也将“现在”视为可以忍受的、暂时的生命历程的特殊阶段。尽管她们“现在”在韩国的生活缺席于“现在”的中国生活, 但却和中国的“未来”生活有关, 现在的“不在场”, 是对自己和子女的未来生活的投资。这样, 中国作为“过去”的空间再一次和自己及子女的“未来”发生联系。朝鲜族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跨国流动, 不仅改变了她们的生命历程, 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 也使她们处于跨国主义双重场景和生命历程连续性的交叉节点。而在这一过程中, 朝鲜族女性不仅品尝到经济成功的喜悦, 也遭遇家庭生活的失败, 但无论如何她们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强的性格品质, 并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生活之间不断重构自己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朴光星。在“同胞”中建构新“族群”-韩国“在外同胞”政策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5) .
[2]赛汉卓娜。另一种移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娘家的家庭战略[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4) .
[3]刘伟江, 丁一。延边朝鲜族地区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研究[J].西北人口, 2015 (2) .
[4] (韩) 李海英。从韩国移住经验看中国朝鲜族已婚女性的认同变迁[J].女性学论丛, 2005 (2) .
[5] (韩) 金贤美。访问就业在中同胞的经验和生活世界[J].韩国文化人类学, 2009 (2) .
[6]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M].New York: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58.
[7]Alejandro Portes, Luis E.Guarnizo, Patricia Landolt.The Study of Transnatioinalism: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J].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9 (2) .
[8]Faist, Thomas.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What kind of dance partners?in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M].edited by Rainer Baub9ck and Thomas Faist.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9-34.
[9]Bruneau, Michel.Diaspora, transnational spaces and communities.in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M].edited by Rainer Baub9ck and Thomas Faist.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Erkmen T.Deniz.Houses on Wheels:National Attachment, Belonging, and Cosmopolitanism in Narratives of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J].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2015 (4) .
[11]Roger Waldinger.The Cross-Border Connection:Immigrants, Emigrants, and Their Homelands[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6.
[12]Elder, Glen H.Jr., Monica Kirkpatrick Johnson, and Robert Crosnoe: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Course Theory.in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M].edited by Jeylan T.Mortimer and Michael J.Shanahan.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 2003:3-19.
[13]Wingens, Matthias, Helga de Valk, Michael Windzio, and Can Aybek.The Sociological Life Course Approach and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M].edited by Matthias Wingens, Michael Windzio, Helga de Valk, Can Aybek.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Springer, 2011.
[14] (美) 范芝芬 (Fan C.Cindy) .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M].邱幼云, 黄河,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52-59.
[15]宁德强, 雷屿。中国农民市民化:跨越30年时空的艰辛变革[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 .
[16]全信子。试析中国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4) .
[17]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社会学研究, 1997 (1) .
[18] (韩) 禹明淑, 李娜英。朝鲜族已婚女性的跨国移住和生命历程变迁[J].韩国社会学, 2013 (5) .
[19] (韩) 郑善荣。外国人力就业现状及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R].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研究报告, 2015:21-22.
[20]李华。家庭策略视域下的中韩跨国家庭研究-以延边朝鲜族为例[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7 (3) .
注释
1 据韩国法务部外国人登录统计报告, 在韩朝鲜族人数从1995年的7367人、2000年的32 433人, 到2005年开始大幅增长达到146 338人, 到2010年达到366 154人, 2012年538 277人, 2013年512 120人, 2014年606 964人, 2015年647 717人, 2017年652 028人。韩国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网站统计资料室统计年报2016年
2 韩国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网站统计资料室统计月报2017年11月
3 据统计, 在1997年末, 延边地区的私营工商户大约有72 000多户, 其中60%~70%是女性经营者, 而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农村女性。另外, 1999年, 在北京的朝鲜族流动人口有5万~6万人, 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吴相顺。朝鲜族女性与女性文学[J].满族研究, 2001 (1) .

